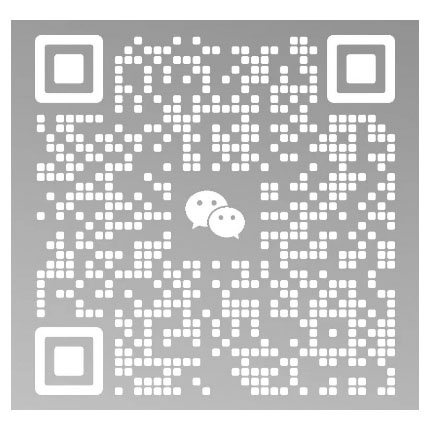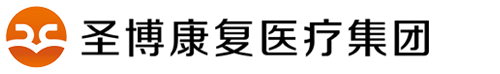
「我在圣博当康复师」。这个「我」,是入职11年的王芳老师,是膝盖积液的孙眉老师,是做梦都在吹泡泡的林园园老师,是被孩子唤作「妈妈」的高合云老师。
这个「我」,是每一个人。
这里讲述的,不是一个人的故事,是我们的故事。是一群年轻人,选择用自己的一双手,去托起另一个孩子、另一个家庭命运的故事,是一个群体的光荣与梦想,挣扎与坚持。
文章有点长,我们试图通过对儿童康复治疗师这个职业的详细解读,让更多人了解、看见,康复师这个职业,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?
编辑|圣博文宣
“妈妈”
2025年8月6日晚7点,圣博康复医院全纳教育的一间教室里,一场毕业典礼正在举行。
晚会开始没多久,来自安徽、在圣博康复半年多的6岁小女孩糖糖,突然抱住她的康复师高合云,清脆地喊了一声:“妈妈”。
一声“妈妈”,让高合云泪湿眼眶。虽然小糖糖在课堂上也经常喊她妈妈,但离别之际的这一声“妈妈”,更让人动容。高合云坦言:“那声妈妈比我自己亲闺女喊的都甜。”那一刻,她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得到了回报。
这是高合云在圣博当康复师的第六年,六年时间,在她手中毕业的孩子有二三十个。每当看到康复毕业的小朋友可以回家上学,回归正常的社会,高合云就觉得这份工作值得她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这个“更多的努力”不是说给孩子上好课,做好康复训练就可以了,它背后还有更多外人看不见的辛苦与压力。
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康复师,给到孩子结果,获得家长认可,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、精力、体力和情感。
而这一切的前提是,你先有资格进入圣博。
百里挑一的选拔
“康复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、包容心,还要有责任心。我以前觉得这几个词挺虚的,干久了之后,我发现这几个词要虚了,还真干不了。”周文玥老师道出了这个行业的入门门槛。
进入圣博做康复师竞争激烈,堪称百里挑一。50多个应聘者中,可能只有五六人能通过面试。即使成功入职,淘汰率依然高得惊人。
现在已是部门负责人的秦凯老师回忆,他来的那一年,与他同期进入科室的有三位新老师,而其中离开最快的一位,仅仅用了三天。
新康复师会面临三个月的考核期,需要通过技术知识、动作和评估等多重考验。即使通过考核,新老师还要获得家长的认可才能开始收费上课。
有些老师承受不住考核的压力,考核期没通过就主动离职。
在圣博,每位康复师都会经历被淘汰、被家长选择的阶段,这也是他们专业成长中的重要一环。
“新老师通过考核后,家长就会给你贴上一个「新人」的标签,你就是新老师。”语言老师孙眉说。
孙眉分享了一次难忘的经历:有一次,排课老师给她排了一个孩子。孩子虽然来了,但妈妈一见她是新老师,就明显流露出不信任。出于对排课老师的尊重,那位妈妈勉强让孩子上完了课。然而课程刚一结束,她根本没心思听孙眉的反馈,拉起孩子就要离开。孙眉赶忙上前,想说明这节课的训练目标和内容,却被对方一句话堵了回来:“有什么可听的?新老师能上出什么?快走,我们去找别的老师。”
那一刻,孙眉站在原地,心里就觉得特别难过、特别委屈。
秦凯老师在谈到自己作为新康复师的经历时说道:“当时排课老师给我排了十节课,结果到了第二周去上课的时候,只来了一个孩子,那一个孩子看到别人不来上课也不来了。”
面对这种情况,大部分老师表示理解家长的做法:“如果换做自己,也想给孩子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”。他们认为,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家长,而在于如何让自己尽快成长起来。
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,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、优秀。
秦凯老师就是这样做的。
“我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性价比。同样一节课,人家上30分钟,我可能给他上50分钟,反正我没有课,我就抓住孩子使劲练。我上一节课,一个孩子,能把衣服全部湿透。就是靠着一个一个孩子去打开自己的口碑。”

当然,在圣博,新老师只要想进步,他就不是一个人。他的身后,是一整套强大的帮扶机制。每一个新人入职,都会配备专门的带教老师,从教学技巧到家长沟通,从理论学习到实操细节,一步步带、手把手教。只要你想进步,就有人全力托举。这种“传帮带”,早已融入圣博的基因,成为这里一以贯之的核心文化。
在传统的观念里,常有“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”的说法,但在圣博,这样的顾虑是不存在的。因为康复是一场协同作战,而非一个人的单打独斗。唯有相互依存、彼此成就,整个团队才能真正强大,最终为孩子带来更好的康复效果。
时间永远不够用
早晨8点,换上统一的工作服,走进教室,把手机放到固定的位置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女老师不能做美甲、戴首饰,所有老师都不能染太鲜艳的头发。
课间只有五分钟休息,这五分钟还要用来和家长沟通。"经常是一上午不喝水,等到中午吃饭时才能喝上几口,因为喝水就要上厕所。"一位康复师解释道,"有的老师上厕所都是跑着去,因为很多时候你这节课还没结束,另一个孩子已经在等着了。"
从外面看,圣博与普通医院没什么不同。但走进其中便会发现,这里服务的全是脑瘫、自闭症、发育迟缓、智力障碍等类型的特殊孩子。
特教老师的工作,远不止上课那么简单。特教老师乔乔形容:“我们不只是老师,更像是家长,给孩子喂饭、哄睡、换纸尿裤、带他们上厕所、擦屁股。有月经的女孩还要帮忙更换卫生巾。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拉肚子,在课外课堂上拉裤子里了,几乎全身沾满了臭臭,老师也需要及时处理。”
另外,给这些孩子上课,并不只是上好课就行,课前必须做好充足的功课。
最开始,新孩子第一次来上课,老师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这个孩子的性格、脾气、喜好、禁忌,包括他能吃的、不能吃的食物,对什么东西过敏等。了解得越全面、越细致,才能制定出贴合孩子实际需求的训练方案。
“我现在带的一个孩子,只吃生淀粉,别的都不行。这种特殊需求,只有细心观察和沟通才能发现。”语言老师孙眉说。
有些年龄小的孩子,上课常常哭闹不止,又不会表达,老师只能一次次把他们抱在怀里安抚。往往一节课下来,要重复十几次,导致课程无法正常进行。
更难的是,康复师必须始终保持专业的状态。“不管你是失恋,还是家里有事,只要穿上康复师这身衣服,你就必须是阳光积极的,必须全力以赴去对待孩子,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” 李健老师坚定地说。
不过,工作中也常有温暖的转机。如果你某天心情低落,却在课上惊喜地发现一直停滞不前的孩子突然有了进步,那一刻,所有阴霾都会一扫而空。“整个人一下子就被点亮了,一整天的心情都会特别好。”李健老师补充道。
即便如此,日复一日的情绪和体力消耗,还是让很多老师感到疲惫。下班回家,常常累得什么都不想做。“孩子也顾不上管,饭也不想做,甚至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,只想躺下来好好休息一会儿。”一位康复师描述。
与康复师相比,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时间往往更长。秦凯作为康复二部的负责人,管理着一个二十多人的团队。每天要开会学习、沟通家长、评估孩子。忙起来,一周只有一天晚上能见到儿子。
“我儿子一岁多,一般九点左右就睡了。上周我最晚一次十一点半到家,平时也差不多九点多,基本上每次回去,他都已经睡着了。"
入职11年的王芳,如今是全人科室的负责人。聊起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,她坦言对孩子有亏欠。
每天下班晚,孩子已经习惯了。偶尔她早回家,孩子反而会问:“妈妈,你今天怎么这么早?”令她欣慰的是,孩子非常理解她,还经常偷偷往她包里放一些好吃的,并告诉她:“妈妈,这些好吃的你带回去哄你那里的孩子吧。”
王芳说,自己能够在工作中取得今天的成绩,离不开家人的理解与支持。正是他们的包容与付出,才让她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

康复师们不仅要服务孩子,还要服务家长。
每天晚上,老师们都要跟家长详细反馈孩子当日的情况,沟通经常持续到深夜。十点、十一点,甚至更晚,只要家长发来信息,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回复。“你要对孩子负责,就要给家长一个交代。”一位康复师这样说道。
每个月,每位康复师都要为班上的每个孩子精心制作对比视频。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分析孩子的进展、总结不足、制定下一阶段的新目标。
有时下班后或是休息日,家长一个电话寻求帮助,老师们也总是二话不说,第一时间赶去帮忙。尤其是那些从外地来、独自带着孩子坚持康复的妈妈或老人,在这座城市无亲无故,康复师便是他们最信任、最能依赖的人。“能帮就一定帮”,这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而是深植于每一位圣博人骨子里的信念。
乔乔老师的男友在异地当兵,两人平时靠电话联系,可她把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孩子和家长,连宝贵的通话时间也常被压缩。提及此事,她没忍住,眼眶红了。
“我的朋友们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:「你出来聚会就不要再聊孩子了。」但是他们已经占满了我的生活。”
把眼泪憋回去
高合云老师回忆,有一天她正跪在地上教一个孩子做趴起动作,突然,孩子后脑勺猛地向后一顶,正好撞在她的鼻子上。
“哎呀,当时疼的我呀,真的不夸张,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”高合云老师回忆道,“但我正在上课,肯定不能喊委屈啊,也不能去擦眼泪。我就一抬眼,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,继续上课。”
在康复训练中,这样的场景并不少见。在圣博,几乎每位老师身上都带着不同程度的“职业印记”。被孩子抓、掐、咬、打眼镜、抓头发是家常便饭。
特教老师张芮凯工作三年后苦笑着说:“我现在两只手应该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。”班里有个孩子,只对他有攻击行为,他自嘲说:“可能是对我情有独钟吧。”
乔乔老师曾经历过更为严重的攻击。“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一个孩子情绪突然失控,当场把我的眼镜腿掰断了。”她带的班里最大的孩子15岁,个子比她还要高一大截。
“这些孩子的情绪有点不太受控,要么就是特别开心然后大笑不止,要不然就是非常伤心想释放情绪,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和发泄。就会出现打老师、抓人、跳跃,甚至伤害自己、伤害别人的情况。”乔乔老师解释道。
这就要求康复师在上课的时候,必须时刻保持警觉,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,留意每一个孩子的情绪变化和动作预兆。
有一次,在做游戏的过程中,一个孩子因为提出的要求未被满足,突然咬住了林园园老师的胳膊,留下很深的牙印。“特别疼,但我不能喊出声。我怕任何过激的反应会让他失去对我的信任,觉得这个老师好凶、好可怕。那样之后,他可能就不愿再来上课了。”
遇到这种情况,老师们通常会先安抚孩子,通过拥抱、转圈等方式转移其注意力,让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。
“课堂上我们不能表现出一丝委屈或痛苦,但下班回家后,有时候真的会忍不住哭出来。因为你要说不疼,那肯定是不可能。那个伤疤就在那,不可能不疼。”林园园老师说道。
更让老师们感到压力的是,某些行为容易被家长误解。
乔乔老师提到,班上一个七岁的孩子,一旦情绪爆发,力气惊人。“我们是为了防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,才试图抱住他,但他一挣扎,很容易就在皮肤上留下红印。有些家长会怀疑是不是老师故意掐扭孩子,这让老师们倍感委屈。”
周文玥老师经历过更惊险的时刻。一次,一名大龄学生突然举起课桌要砸向她。“当时心里真的非常害怕,但我告诉自己,就算演也要演的自己不害怕,镇住他。一旦我表现出恐惧,他可能会觉得这个行为有效,下次反而更激烈。”
还有一次,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试图动手打别的小朋友,周文玥赶忙上前拦阻,却被孩子猛地抱住腿狠咬了一口。“那一块全紫了,十一岁孩子的咬合力,真的不容小觑。”

青春饭
圣博的康复师治疗师平均年龄二十七岁左右,原因很简单:这是一项极度消耗体力的工作,甚至被不少人称作“青春饭”。
在早期康复部,孩子们大多身高不足一米,各方面能力弱、配合度低。老师必须长时间保持跪坐或弯腰的姿势,在地板上训练。秦凯老师回忆:“我去早期康复部上课不到半年,有一天下班,突然感觉腿脚发麻,整个人都懵了。我心想,该不会是腰椎间盘突出吧?”可他最终没有去检查。“查了出来反而更难受,不如不查。疼一阵,熬过去就习惯了。”
这种“回避”成了许多康复师心照不宣的应对方式。“查出来又怎样?突出是不可逆的,但我们每天还是要坐地上、弯腰、迁就孩子的体位,牺牲腰椎颈椎,几乎不可避免。”
PT(物理治疗)老师常常一个姿势保持十多分钟,腰部劳损已习以为常。不少老师贴着膏药坚持上课,只为了以好状态面对孩子。言语老师一天下来嗓子经常是哑的,感统老师则可能一跪就是一中午,教孩子爬行、支撑。
康复师孙眉的膝盖问题更加严重:“我的膝盖不太好,拉伤、积液、增生……每天不是跪着就是趴着,不停切换姿势。”最严重的一次,她突然走不了路,只能躺在床上,连起身都困难,不得不请假休息。
“这算是职业病吧,”另一位老师补充道,“腰椎、颈椎、腱鞘炎……太常见了。
如今,不少老师都悄悄戴上了腰托、贴上膏药,继续每天的康复课程。他们用身体的损耗,换回孩子们一点一点的进步。
“不敢”与“不忍”
在圣博,老师们有一个默契的共识:除非实在病得撑不住,否则绝不轻易请假。
原因很简单,每一次请假,都可能耽误一个孩子宝贵的康复时间。“家长大老远赶来,把圣博当作最后一站和唯一的希望。如果我们耽误了课,良心上真的过意不去。”几乎所有老师都这样说道。
一位老师坦言:“每次发信息请假,我都要反复说「不好意思」。家长通常表示理解,可我心里还是觉得亏欠。”
很多家庭为了孩子康复倾尽所有,有些甚至卖了房子、借遍亲友,才勉强凑出康复费用。秦凯老师所在部门曾有一位家长,有一天,突然来找秦凯请假,说要带孩子回老家一个月。
秦老师有些意外,这么长的假期,课程名额很难保留。他忍不住追问:“怎么突然要回去这么久?”
家长沉默了一会儿,低声说:“秦老师,您一定帮我留个位置。我回去借钱,再借半年,继续康复。”
“一个家庭到了卖房这一步,几乎就是孤注一掷了。如果我们不用心,怎么对得起这份托付?”这份近乎决绝的信任,重重压在老师们的心头,却也化作最坚定的力量。 “良心和善良,在这个行业太重要了。上课的每一分钟,我们都不敢浪费。”
比请假更让老师们难受的,是目睹孩子进步缓慢。刘昶鑫老师说:“很多家庭掏空积蓄来做康复,如果半年、一年却看不到明显变化,有的家长也许就要放弃了。那个时候,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我们真想给他们更多、更好的结果。”
正是这份沉甸甸的责任,让圣博人始终恪守着一个承诺:绝不收取家长任何形式的礼物。
“家长们的信任,已经是最好的礼物。”一位老师这样解释。
有时家长会把东西放下就走,老师们也会以高于原价的方式回赠。李健老师说,他们部门有个新加坡的孩子,买了不少零食放在医院,就和妈妈坐飞机离开了。等过段时间孩子回来,康复师们准备包了他的所有晚饭,一星期点一回他喜欢的临沂炒鸡。
李健老师还收到过家长发给他的5000元红包,发了三次,都被他婉拒了。有家长买了西瓜送到推拿科室,老师给送回去,家长拿刀一切两半,又送了回来。
对老师来说,不收礼不是制度,而是本分。正如一位老师所说:“收了,心里会非常非常不舒服。”
从0到1
康复是一个从0到1的漫长过程,有些孩子一个月可能只前进了0.1。
有的孩子学走路,你看到他迈出两步,但这两步背后,是老师几个月、甚至几年一遍又一遍的诱导、构建和练习。“就像盖房子,地基必须反复夯实,楼才能稳稳盖起。”李健老师这样形容。

有时候一个动作要重复几百遍、上千遍,才能慢慢刻进他们的身体记忆里。周文玥老师提起那些“倒退型”的孩子,语气中带着深深的无力:“明明付出了全部,却不一定看得到回报。”
在圣博,每一位老师的口碑都不是凭空而来,也不是由领导认定的,而是家长一点一滴“捧起来”的。“家长觉得你行,能给孩子带来希望,你才是真的行。如果家长不认可,再高的职位也只是虚名。”秦凯老师这样说。
许多家长带着孩子走南闯北、试过无数机构,一节课就能看出老师是否用心、专不专业。“你说得再动听,不如课堂上做得扎实;你做得再认真,也不如孩子实实在在的进步有说服力。”
于是,老师们常常下班后仍留在教室,与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,直至晚上九点多。“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。” 一位老师苦笑道。
有的老师甚至一个月上了500多节课,平均每天超过二十节。然而,高强度的工作之外,他们还要持续学习、不断创新。每周雷打不动的培训学习与案例研讨,是圣博坚持多年的传统。经常晚上九点、十点,教室的灯还亮着。

特教不仅需要耐心,更是一个融合教育学、心理学和康复技术的系统工程。年轻的林园园老师道出了许多人的日常:“空闲时跟着资深老师看课,不懂就问,周末在家看资料自学,要学的东西,永远没有尽头。”
“王院长本身就是技术出身,要求极高。一开始都是他手把手带我们分析孩子、研究动作。”王芳老师回忆道。如今,医院仍经常派老师去北京、上海等地学习,回来再分享传授。“一切都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帮到孩子。”
更让人触动的是,即便有些孩子评估后没有选择圣博,老师们仍愿意接听家长的咨询电话、提供建议。“不管他来不来,只要我们知道的,能帮就帮。”这份善意,源于王院长一直倡导的“对每一个孩子负责”的理念。
为什么还在坚持?
这份工作并不轻松,处处充满挑战。为什么他们还在坚持?
所有老师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同样的答案。
成就感,是他们最大的动力。
刚入职三个月的言语老师闫笑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:“我真的特别喜欢小孩子,圣博这个平台非常吸引我。在这三个月当中,我感受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成就感。”
李健老师说:“当一个孩子从无法站立,到颤巍巍迈出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,那一刻,感触是最大的,所有付出都化作巨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。那是我最开心、觉得这份工作最有价值的时候。”
林园园老师分享道:“从我开始代课到现在,我能看到我手里有几个孩子已经毕业了。他们回到了正常的幼儿园,融进了普通的小学。那种荣誉感,无法用言语形容。”
刘昶鑫老师也有同感:“当看到孩子在你手里从零开始,什么都不会,慢慢变成一变成二的时候,就感觉所有付出都值了。就好像,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作品一样。”
孙眉老师比喻道:“就像是自己亲手培育的一盆花,他开花了,那种激动,那种喜悦,难以言表。”
有时候,进步就发生在一瞬间。一位老师动情地说:“你教了无数次,他好像一直没学会。可就在某个无意间,他突然做出来了。那种心情,真的会感动到想哭。那么久的坚持,终于没有白费。”
孩子温暖的举动也是支撑他们的重要原因。周文玥老师笑着说:“前两天我胃疼,有一个小姑娘过来说:‘老师,你为什么捂着这个地方?’我说我肚子不舒服,她说:‘那我抱抱你,抱抱你就不疼了’,就很可爱。他们不发脾气的时候都是天使。”
乔乔老师说,每当收到家长的感谢信,或者家长送来的锦旗,那种认同感和荣誉感,“真的什么都替代不了”。

推拿部的李军老师还提到了来自家长的温暖关怀:有时候加班,连饭都顾不上吃,家长就会说,“你不要嫌弃,我上去下个面条给你吃,工作再忙也得吃饭”。特别是那些大姨,总像心疼自家孩子一样心疼老师:“吃饱了,才有力气干活。”
更深层的动力,源于一种使命感。
版权所有 © 2023 临沂圣博康复医院 版权所有 鲁ICP备16020008号-1 后台管理
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